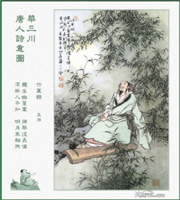王維承繼莊子的思想,以閒適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生活注重清閒,寫詩歌頌閒逸,以擺脫〝塵勞〞和〝形役〞為生活取向。
歷來有不少人批評王維消極和自私,其實不然。王維的生活模式以道為體,以禪宗的觸目而真的精神為基礎,以莊子的〝大同而無己〞觀念為歸宿,追求自由。
古人非傲吏 自闕經世務
偶寄一微官 婆娑數株樹 《漆園》
古時讀書人,學而優則仕,即是當官。王維放棄做大官,寧願做一個小官,偶寄一種悠哉樂哉的生活,與幾棵樹相伴,回歸自然。自魏晉以來,因為社會動盪,多數文人都追求漆園的人生取向,以〝輕〞的自由生活代替〝重〞的功業追逐。
王維從幼跟母親事佛,深受佛理佛法的規範。佛教傳入中國與儒道融合,成為禪宗,以虛靜為理想境界,以悟為慧。悟甚麽呢?悟識自己在宇宙間的意義,在大自然間的地位和應有的作為。用二十一世紀的話講,即是〝認識自我〞及感知〝我是誰〞的大問題。
萬物有情
道家主張〝與物為春〞(《莊子‧德充符》)及〝萬物復情〞(《莊子‧天地》),肯定人的情感性靈,重視主體人格的絕對自由,叫人不逃避自然,而要深契自然以達到混同自然一體的境界。王維作《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表達了他這些方面的認識:
寒山轉蒼翠 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門外 臨風聽暮蟬
渡頭餘落日 墟裡上孤煙
復值接輿醉 狂歌五柳前
第五句的餘字和第六句的上字都是詩眼,富於包孕的情趣和動態意蘊,寫照詩人的〝閒〞的活動結果。現代人用半杯水的現象說明人的心態,樂觀者說〝我有半杯水〞,悲觀者則說〝我只餘下半杯水〞。王維以閒情觀世,不因落日而趕着渡船,而欣賞其中的景色。而墟裡的孤煙不正在冉冉上昇嗎,不見日盡的殘象。這都是積極的審美態度。
全詩以寒山、秋水、落日和孤煙的季節時間特徵,寫宇宙中的虛靜情景,引讀者進入一種神超理得的閒適詩意生存之中。我們今天身處熙攘的都市環境,心受多方面的壓力,如果坐下來呷幾口茶,欣賞王維的那種閒情逸趣,可以即時減壓,不用吞丸仔了。
事在人為
孔子觀照人生,說甚麽事情都〝無可無不可〞,事在人為,適意而為。這是一種務實而情意平衡的做人態度,持着它,我們不會執着〝人定勝天〞那種狂妄心態去凡事求勝,不論成敗都給自己和他人强加心理壓力的。現代西方甚麽都講競爭,把人生推向極端矛盾,使成功的人和失敗的人都沒有和平的歸路,實在不幸。消費主義社會更製造像足球競賽那樣的戰鬥,讓冠軍隊伍的居地百萬人上街慶祝,有時造成悲劇。那種自己不〝勞〞而慶幸勝利的心態,除了給商家製造厚利之外,不知有何好處?
守閒愉悅
莊子的守閒或歸閒精神有兩個條件,一是〝齊物我〞,二是〝齊彼此〞。前者勸人破除自我中心優越而混同於物,成為一個萬物中的〝生態位〞,與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齊位。後者勸人遊心於萬物之間,平等對待他人,不累私心,取得無累的自由。如是說,〝閒〞是一種幸福。王維寫他的幸福情感,給我們留下《青溪》一詩:
言入黃花川 每逐青溪水
隨山將萬轉 趣途無百里
聲喧亂石中 色靜深松裡
漾漾泛菱荇 澄澄映葭葦
我心素己閒 清川淡如此
請留盤石上 垂釣將已矣
試想青溪有何魅力呢?叫詩人從中體驗到閒的愉悅?內情(the catch)在於詩人平日的心態與大自然的景物和諧一致,使他見到一條平淡簡單的青溪即會心解意,共鳴知意,生出快樂。詩人說,〝我心素已閒,清川淡如此〞。假如換一個人,平日心煩意亂,不有所歸,青溪就不能成為他會心的心靈原野了。
王維的愉悅和幸福是一種禪悅,一種從審美活動取得的純真歡喜。最多人熟悉的《鳥鳴澗》和《辛夷塢》都以〝閒〞字為詩眼,寫詩人內心的主觀的閒境超越外在世界的任何動靜,所以,人閒和花落本來不成因果的兩樣東西,亦變為互為因果。
人閒桂花落 夜靜春山空
月出驚山鳥 時鳴深澗中
因為詩人心閒,所以可以看見桂花飄落的美儀,亦可以聽見花蕊落地的欵欵音響。這些靜中之美不是一般人所可以體驗得到的,必須要通過修養,達到莊子說的〝忘適之適〞,方能做到。西方心理學苦求認識莊子的〝忘〞和〝空〞,作為感知絕對自由和快樂的途徑。我的許多心理學家朋友在深厭事業角逐的活動之時,苦修靜坐,以求達至一種心靈的〝高峯經驗〞(peak experience),看通世界。可惜,他們看錯了路,苦苦走了,卻不見原就不明的目的。
放下自我
要知道莊子說〝忘〞,不是forget或negate的意思,而是放下的意思,放下自我中心,自我為是,自我求有等〝你死我活〞的競爭,回復人與大自然的平和相生,共同進退。有了這種智慧,就〝無為又無所不為〞了,即無所不能為。每個人若然盡己所能,接受自己的成就,就滿足愉悅了。
王維有一首《書事》的詩這樣說:
輕陰閣小雨 深院晝慵開
坐看蒼苔色 欲上人衣來
小雨過後的庭院一派清新幽美景色,叫閒人感到物我渾然一體,忘卻塵世的喧囂和生活的得失榮辱,閒心此在。詩人在這裡移情物上,明見雨水洗潤以後的青苔異常青綠,〝欲上人衣來〞。在幻覺以外的現實中,究竟靜態的青苔活潑地要染上人衣,抑或詩人賦予它走上人衣的異常,生命動作?一切都有可能造成了無限,給讀者提出多向的暗示,叫他隨意進軍藝術玄妙的無盡前路,各取其所。
王維的〝環保〞意識特强,早就以青綠色為最美的東西。《鹿柴》的〝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木蘭柴》的〝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萍池》的〝靡靡綠萍合,垂楊掃復開〞,《田園樂》的〝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都突出綠色的至美,寫下他對生態的理想及對和諧的渴望。
閒坐悟智
王維時常提及閒居淨生的樂趣,其中閒坐是他生活方式的重要部份,下面兩首詩說明其趣:
獨坐悲雙鬢 空堂欲二更
雨中山果落 燈下草蟲鳴
白髮終難變 黃金不可成
欲知除老病 唯有學無生 《秋夜獨坐》
竹徑從初地 蓮峰出化城
窗中三楚盡 林上九江平
軟草承跌坐 長松響梵聲
空居法雲外 觀世得無生 《登辨覺寺》
現代人已經失去閒坐的可能了,多麽可惜。人們不是坐下來便扭開電視,便是致電與人講話,不管有無內容。似乎,從幼年開始,現代人已經沒有獨立靜坐的能力,父母們好像最怕孩子寂寞,如果自不能陪伴小孩,亦要用大堆公仔和玩具堆塞在他們的搖籃,不知為了甚麽。
禪宗內涵教與學的道理和方法,比現代心理學更為貼切人的心智作用。一個人在靜坐的時候最能認清自己,以及個人與他人和環境的種種關係,從而抱樸見素,生成和諧安穩的生活智慧,保持心理平衡。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畢生尋找自我,得到這樣的結論:〝人與他人交往,面對的是人群的一部份,而在獨處之時,他面對的是整體和萬物之源;這種體驗便是廣義的宗教體驗,直通人之為人的絕對自由。〞現代人如果有意尋得生態意識的醒覺,認清自我,靜坐是最有效的方法。
恬淡自足
人與自然渾為一體的生態追求在王維的詩中頻頻出現。他遠道訪友不見,一點也不奧喪,反為欣賞友人所居住的生態環境,寫下美麗的詩篇,如《春日訪呂逸人不遇》。詩云:
桃源一向絕風塵
柳市南頭訪隠淪
到門不敢題凡鳥
看竹何須問主人
城上青山如屋裡
東家流水入西鄰
閉戶著書多歲月
種松皆作老龍鱗
這詩所反映的,正是王維所持的無求無待無心的恬淡自足,當他把生命融入大自然的大體之內,即同時實現了生命有限形式的無限超越了。
王維親和自然的實踐是以儒道釋三教的生態智慧為根基的,只有順應自然的覺性,沒有物種的優越感,不有凌駕或征服萬物的絲毫意圖,只視自己為萬千物種中的一種,萬千生態位置裡的一位,委順自然,適應人生。用現代定義界說,王維是一個純粹自然中心主義者。他的《戲贈張五弟諲三首》充份表露了他的生活狀況:
我家南山下 動息自遺身
人鳥不相亂 見獸皆相親
……
青苔石上淨 細草松下軟
窗外鳥聲閒 階前虎心善
王維以悲憫情懷擁抱自然萬物的生命狀態,身心潛入融和,形成生命大智慧朗照地反觀外物,與其他生命同享幸福。所以,他可以感覺到野花開放的愉悅,谷鳥一聲的幽意,飛鳥逐前侶的溫馨,和紛紛開且落的靜穆和淡泊。他的體驗得益於禪宗和道學的體驗,深入自然美的深層,造化的核心,寫出登峯造極的山水田園詩篇。
王維的山水詩有兩種基本類型,一是〝大謝式〞的,另一是〝王維式〞的。前者呈現自然通脫、新奇幽清的美學氣象,營造清空意趣,追求天生麗質的自然原生態,〝興來每獨往〞,〝玩奇不覺遠〞。後者是簡化、虛化和淨化的寫意,一種〝宴坐〞而感的山水小品。詩人表露他自己對山水的感悟,捕捉自然的剎那景況,僅僅表現一種氛圍,一種天然得味,自由的天地精神。
不論是哪一類,不論是寫實或寫心的剎那體驗,詩人都敍表一種物各自然的生態氣質。王維寫詩不以主觀知性的邏輯介入去表達景物原生命的生長和變化姿態,而着意景物的自然興發和演出,呈現物象自身的律動和生機,於自然的靜默剎那感悟宇宙的永恆。我們看《辛夷塢》便見此意:
木末芙蓉花 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 紛紛開且落
王維深得三教的智慧,在生活中到達了〝人已非人、物我同性〞的與大化同在的生命境界。他對山水自然美的體驗進入到禪的空寂悠遠,到達了深邃玄冥的境地。他寫無心,偶然,無思,不慮的直覺印象,可以從《竹裡館》一詩明見:
獨坐幽篁裡 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
詩人在大自然中精神受染,情感衝動,自然地發出抒發的聲音。他接受了〝我〞有許多東西不知,因為〝我〞只是宇宙間一時出現的小小生機。而月亮永恒,知道的多矣。這是一種由悟而生的高度生命自由,亦是人生智慧的至高表現,在閒中出現。今天,我們從他的詩中欣賞這種放之千秋的智慧,亦可閒適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