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風催生英文新詩
沒有勝利的屠殺
英國人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說:〝一次混蛋的、血腥的殺害一整代青年人的戰爭,由一代充滿仇殺意識的軍官指派。〞
面對七十五萬青年被犧牲的事實,史家和大眾一致認為,1914 – 1918年的世界大戰是人類最大的過錯,它只建立了一個大量屠殺的基礎,為二十年後發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做足準備。
〝那些逃過鐵絲網和機關槍子彈經驗的生還者變成瘋了,或者成為詩人。〞有史家這樣總結。
我記得讀初中的時候看電影《西域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最得的印象是,在學校讀書的青少年,都在無奈又充滿報國的心情中準備走上戰場。然後,蒙太奇一轉間,一些疲倦不堪又目光無神的生還戰士,如何走在鄉村小徑上,面對熱心要擁抱他們的姑娘們,毫無反應。他們的心中只填滿着恐懼和無力的怨嘆,對於個人的生還感到深切的抱歉。
戰後,這些生還者寫下大量的詩,有些由他們在戰壕裡寫下的日記整理而成,有些寫他們對人類愚蠢的控訴,有些對未來雋注奇的憧憬,對於明天更好不懷信心。
如今,差不多一個世紀以後,我看電視的戰事報導,再見不到對士兵心理和傷痛的描寫,有的是平民的哀號和死亡,而機關槍早上被導彈所代替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出現的汽油火槍,被稱為化學武器,而今的卻是穩形的細菌武器了。假如1918年的詩人寫的是戰爭的愚蠢和毫無用處(foolishness and futility),那麽,為何今天的總統和將軍每出現在鏡頭面前,都表現着那麽威風和滿懷正義的模樣呢?
史書記1914年的戰爭為〝偉大的戰爭〞(The Great War)。正面的描述說它為了興起民主政制以代替帝國主義。反面的描述諷刺它是西方的虛偽,因為一百年後的今天,英皇的皇冠仍然裝飾着加拿大和澳洲的一些莊嚴國家大事。而美國的武器毫不掩飾地覆蓋全球的每個角落,打着民主平等的旗幟。
今天,沒有戰爭被冠上〝偉大〞的名字了,因為它已經被接受為平凡日事,出現在每日的〝今天新聞〞之中。
詩靈求意
就在那歐洲人深切感到愚蠢與無奈的狀況中,一代步入中年的詩人開始反叛舊思維的妥協和死板,希望尋着詩的新方法和新意境,幫他們減褪時代的疑惑,創生寄望。他們既然對歐洲文明感到失望,自然希望越過海洋與文化,到古老中國尋寶,體會方塊字的魅力,老莊智慧的安心方法,禪的自然自在,以及這些智慧在中國古詩的千恣百態的呈表。簡言之,他們馳騖中華文化的安心和滿足。
由儒、道、釋合一而成的中華文化,對於生、死、時、空、以及人與宇宙陰陽動力的互相作用,都有獨到的解釋和調和方法,把人放在主宰生命的主位,脫離恐懼、憂心、絕望及無奈。這些智慧正是艱苦地逃脫戰火的〝被劫者〞的精神救星。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英語世界,來回美國、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文人輩出,不勝枚舉。那是一個眾人尋求精神出路和藝術創新的大時代。本文畧舉三位與中華文化關係密切又充滿創新動力的詩人,龐德(Ezra Pound),洛威爾(Amy Lowell)和埃利奧特(T.S. Eliot),都是影響詩壇文壇深遠的名家。
 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的一生最為複雜多樣。他是意象主義(Imageism)的創導人,畢生與詩和詩人為伍,反對戰爭,馳騖中華文化,卻又在離開美國和英國到意大利定居以後,聲明擁護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結果在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被判入獄,最後被關入精神病院,脫離死刑。他活到87歲,即使在生命絡結之前的二十年間,亦寫下大量詩文,並贏得數十位名詩人和文人的友誼,對他的文采和新詩倡導動力給予最高的評價。
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的一生最為複雜多樣。他是意象主義(Imageism)的創導人,畢生與詩和詩人為伍,反對戰爭,馳騖中華文化,卻又在離開美國和英國到意大利定居以後,聲明擁護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結果在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被判入獄,最後被關入精神病院,脫離死刑。他活到87歲,即使在生命絡結之前的二十年間,亦寫下大量詩文,並贏得數十位名詩人和文人的友誼,對他的文采和新詩倡導動力給予最高的評價。
他自己追求中華文化,做了可貴的翻譯和出版,卻可惜沒有尋到安心。主要原因也許因為他不懂中文,不能深入中華智慧的精髓,也許因為他身處大時代,而且是歐洲人嘗試步入現代的矛盾時代所受衝擊太大。他臨終前宣佈:〝我一生努力,卻為怨恨所牽霸,不論做甚麽都搞成一窩泥漿,不少事情出於偶然。〞這不是謙詞,亦非託詞,他五十歲以後逐漸患上精神分裂症。
俗人不知,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數都聰明過人,而且勤奮向上。龐德自學中文,臨終之前仍然身帶《論語》和中文字典。
龐德於1915年出版由十四首古詩組成的《神洲集》(Cathay)這些詩不是他譯的。他的一位朋友田諾羅薩(Ernest Tenollosa)從日文版把這些詩譯為英文,於他逝世之後由他的遺孀交給龐德處理,最後由他改寫成書。
龐德用了很大的努力出版《神洲集》,為了呈現中國詩的意象美和禪道,他希望幫助同代人認識中國式的冥想和友誼情懷,對抗暴力殘殺,進行個人及集體的反思。
英文新詩的誕生
 《神洲集》面世五年以後,意象派新詩(Imageism)出現第二位先鋒,詩人洛威爾(Amy Lowell, 1874–1925)。她出身豪門望族,一位姊妹是著名天文學家,另一位兄弟是哈佛大學校長。她為了提倡意象詩和由自詩(free verse),在大西洋兩岸推廣以中國詩為榜樣的詩藝和詩意,極力反對當時在英語世界流行的喬治亞浪漫式詩體(Georgean Romanticism)和維多利亞時代精神(Victoriam Spirit),力陳它們自大和固步自封,不能迎應新時代的需要。作為這些舊體詩的代替,她努力翻譯,並運用她的財富出版英譯的中國古詩,推動英語詩革命。為此,她與艾斯庫(F. Ayscough)合作翻譯了一百五十首中國古詩,命名《松花箋》(Fir-flower Tablets)出版。
《神洲集》面世五年以後,意象派新詩(Imageism)出現第二位先鋒,詩人洛威爾(Amy Lowell, 1874–1925)。她出身豪門望族,一位姊妹是著名天文學家,另一位兄弟是哈佛大學校長。她為了提倡意象詩和由自詩(free verse),在大西洋兩岸推廣以中國詩為榜樣的詩藝和詩意,極力反對當時在英語世界流行的喬治亞浪漫式詩體(Georgean Romanticism)和維多利亞時代精神(Victoriam Spirit),力陳它們自大和固步自封,不能迎應新時代的需要。作為這些舊體詩的代替,她努力翻譯,並運用她的財富出版英譯的中國古詩,推動英語詩革命。為此,她與艾斯庫(F. Ayscough)合作翻譯了一百五十首中國古詩,命名《松花箋》(Fir-flower Tablets)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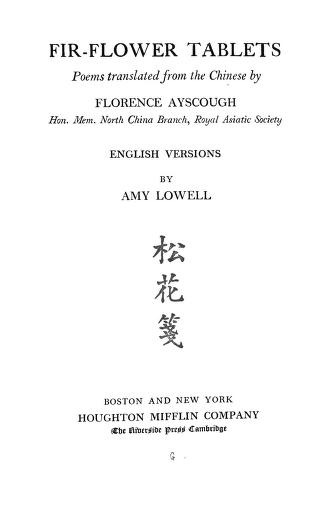
這些詩,包括李白,杜甫,王維和另十位詩人的名句,意象清晰深遠,用字簡練,即使寫成英文,亦美勝松花。詩集在即時的英國和美國詩壇掀起翻天波濤,叫英語世界的學者嘆為觀止。
意象是中國傳統文藝理論的核心概念。《文心雕龍》載:〝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說明意象在心不在物,是人心從客觀世界攝取加工而成的意念形象。詩人借助客觀物象表現自己的主觀情意,內涵詩人審美的淘洗、情感的染色、及意向的化合,表呈理想人格。它是一種創造,自由又主觀,充滿追求崇高的活力。可以想像,對於當時大西洋兩岸的青年詩人來說,這種創造活力有多大的刺激作用。
我們今天翻動歷史,不能不佩服古人的革新動力,像洛威爾那樣出身富貴人家的女性,她為了推動一個新的觀念和方法,即以無限的勇政和毅力,跨越地區、文化和語文,借用中國詩的魅力為她自己的時代豎立新詩的里程碑。
在《松花箋》的序裡,她劈頭便聲明〝我不識中文〞,然後解釋,為了開闢〝通向中國那壯麗莊嚴的世界的路徑〞(A pathway to that magnificient world),她與認識中文卻不懂寫詩的艾斯庫女士合作,兼查字典,譯寫成《松花箋》的妙句。
讀了這些詩,歐美人的震憾不單在見到人性自由的原始(與大自然同在)的呼喊美聲,而且體會到中國的〝樂感文化〞和〝安心文化〞。比對着歐洲人以基督教為基礎的《罪感文化》,中國文化所尊敬的人的自由自主及安心滿足,只有此岸(當下)的可能和奮鬥,沒有彼岸(天堂)的贖罪和約束,給歐洲人提供了新的自由和希望。
自由詩無需死守古詩的規範,只求意象清晰。它的理論來自心理學家伯格森(Henry Bergson)。他在《時間與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裡探索人與時間的關係,說明人的意志本質自由,不由上帝的意旨凌駕其上。在現實中,人與時間為伍,人的最大自由發生在他的靜謐中,即如靜坐,不受任何東西所干擾,包括時間。
 就在這樣的大時代與新思潮的景狀中,詩人埃利奧特(T.S. Eliot, 1888-1965)宣佈:〝詩人就是詩的媒介〞。同時,他又說:〝當今的作家是最大的集體,他們從死人集體中誕生,亦為人的無辜犧牲發出控訴。〞
就在這樣的大時代與新思潮的景狀中,詩人埃利奧特(T.S. Eliot, 1888-1965)宣佈:〝詩人就是詩的媒介〞。同時,他又說:〝當今的作家是最大的集體,他們從死人集體中誕生,亦為人的無辜犧牲發出控訴。〞
新詩情意遠
埃利奧特於1922年發表《荒地》(The Waste Land),由436行詩所組成。二十五年以後的1948年,他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文學家。那是一次特別盛大的慶典,因為瑞典皇家學院的頒獎演詞不同平常。演講者用了一篇特長的講話說明,該次文學盛會不在獎勵一個人,而在慶賀一個文學時代的轉變。
演詞說,二十年前出現的《荒地》的四百多行詩所說的話,要比一部四百多頁的小說所說的更多。它說明當代(西方)文明的荒蕪和無能,同時預述了人在原子彈陰影下生活的無奈與踟躕不安。它呈現一首由字構成的冥想樂曲,預告一個詩的新時代的來臨。它像一座高山從海面升起,光潔,花崗岩的,無裝飾的,由突然展照的一縷陽光所照顯,沒有時限。
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原子彈的殺戮果然於1945年出現,而戰後以來的世界,自稱文明先鋒的美國動用最先進的武器,在全人類的大小社區維持秩序或者進行殺劫。怪不得當年英文世界的文學權威宣稱,《荒地》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詩作之一。
在詩與文學的近代發展史上,T.S. Eliot 的名字是我的同代人的鐘聲,幾乎所有大學生,不論專門,都喜歡讀他的詩、文或者時評的,尊敬他對現代文明的卓見。及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現的〝岩山詩人〞和〝節拍一代〞(beat generation),都是意象詩和新詩的忠誠繼承者。用龐德的介定說,意象主義是:〝那些呈現一個時間片刻的智知和情感心結的詩句,用通俗的字,創新的韻律,自由的題材,清晰毫不含糊的符號,濃縮的意義。〞
試看 T.S. Eliot 的《空洞人》(The Hollow Men)的九十八行詩的最後的控訴力:
這是世界告終的式樣
不有巨響只有嗚咽
意象的塑造
中國古詩慣於排列一些用來表達具體事物的名詞,不用聯結詞或方位把它們串連一起,像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英美意象派詩人看上了這一特點的美意,在翻譯和創作上作出大膽的藝術嘗試,為英文詩開拓了意境無窮的新景象。
龐德把李白的〝驚沙亂海日〞妙句譯為:
驚奇
沙漠的迷惑
大海的太陽
他的《雨中旅途》說:
雨
空曠的河
一個旅人
……
秋月
山臨湖而起
一九一一年某日,龐德站在巴黎地下鐵路的月台上,猛然閃出一個念頭,把當時所見所思寫成《地鐵月台》(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最初寫了三十行詩,半年後改為十五行,一年後改為兩行。詩云:
人群中幽靈般的臉面
潮濕的鐵枝條上的花瓣
原文兩句十四個字的簡潔詩,把他所瞥見的一幕,敍述鮮明清晰,刻劃出都市人們那千體一律的無表情的形態。這是意象派詩的佳作。
龐德翻譯《論語》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用創意十足的想象,把〝習〞字折為兩段,譯(寫)為
學習
時間讓白色翅膀帶走了
怎不叫人高興
洛威爾寫《日記》,運用中國詩對意象的描繪,和美國人對情感的坦露,創出英文詩的東方魅力。詩云:
狂風搖撼樹枝
銀燈在綠葉間顛蕩
老人低回追尋
年輕時愛情的夢影
她寫《中年》用穩喻着色,力求繪出明確的意象。詩云:
像黑色的冰地
由莽拙的溜冰者
劃下無條理的圖式
我陰暗的心面
流行歌的魅力
龐德和洛威爾都是性格倔强的人,他們在提倡意象詩的數十年間,合作了又各建堡壘,以及聯絡同心人壯大各人的門派。在這過程中,世界變化千萬。宏觀看,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贏取了大量財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更藉着消費主義獨霸全球經濟利潤。可惜,這些財富都半數用作軍費,四出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打起〝自衛〞或者〝維護民主〞的旗號。
在大西洋的彼岸,在歷史上豪稱〝米字旗無落日〞的英國,則在一百年間從强國變為〝苟延〞之國。如今,英國公民由許多前殖民地的有色人種組成,他們對於原英國人反對移民入住英倫三岸的呼聲,展開一個有力的旗號,上書:〝我們在這裡,因為你們曾到我們那裡。〞(We are here because you were there)說明侵畧者終有自吃惡果的時光。
不過,歷史公平,英文世界的前衛詩人彷照中國古詩和生命智慧興起的意象詩和新詩,仍然花繁果盛,以流行歌曲(popular songs)的型式高歌大眾心聲。美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陷入越戰,不能自拔,叫青年人遠去毫無關係的地區送命,而生還者則受虐於終生的身心殘廢。名歌手鍾‧貝茲(Joan Boez)的許多流行曲都詞意深雋,直達人們的靈魂深處,如《花兒去了哪裡?》和《我們一定克服困難》(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We Shall Overcome) 等等。
與此同時,被稱為〝歐洲紐約〞的利物浦(Liverpool),歷來染着有色人種移民的多元文化傳統,驟然出現〝四披頭〞(The Beatles)的四位青年歌手。他們即時征服世界,並為祖家贏得〝流行歌曲的世界首都〞的稱號。他們自作自彈,以響亮而喊出時代心聲的詞曲為人類呼起一個美不勝收的新時代。他們的《明天永不知道》和《我有一個感覺》(Tomorrow Never Knows),(I’ve Got a Feeling)等歌詞。為英文新詩注入新鮮如朝露一般的靈魂安撫劑。他們的創舉叫英女皇立即破例頒封他們為英國貴族。
等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有英語專家研究四披頭歌詞,指出它為現代英詞開創了新語法,表意率直明亮,叫大眾每念起來感到親切貼心。
社會發展與文藝。創新同步馳前。今天,通訊科技發達,多數人都已經不讀詩和作詩了。人們甚至連看傳統文字亦覺得不耐煩,改看簡寫的〝手機語文〞。我們很難預見這種趨向的前景,但是,歷史不以十年、百年計算,不同文化的交差影響更是持續而恒久的。
今天,如果你去英美著名大學的圖書館查看文學的〝活頁檔案〞,肯定容易看見寒山的《眾星羅列》。它以澄碧明月的景觀,表現月華的靜潔境界,以示禪心的空明自由,安撫二十一世紀青年人的迷惑心靈:
眾裡羅列夜明深
巖點孤燈月未沉
圓滿光華不磨鏡
掛在青山是我心

